细说从头•辞书的故事(8):
一典在手,读写不愁
汪惠迪
1979年5月前,笔者在国内教书;其后,在境海外专事文字工作。作为语文工作者,少不了要用词典,到退休时,所置备的辞书大大小小有数十部。以成语词典为例,从《汉语成语小词典》(商务版,1955年)到《汉语成语辞海》(武汉版,1999年),不下20部。
 《汉语成语辞海》
《汉语成语辞海》
(199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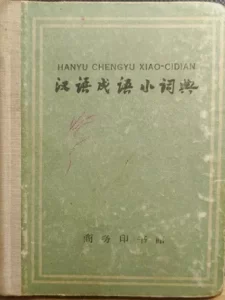 《汉语成语小词典》
《汉语成语小词典》
(1955年)
2022年商务印书馆125周年馆庆时,我应邀写了篇祝贺文章——《词典,我永远的老师》。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工作时,几乎每天都会遇到语言应用上的问题。比如有读者来电问,成语“拾级而上”怎么读,是“固步自封”还是“故步自封”,“感冒”的“冒”字和“小”字怎么写,等等。
有的问题,令人莫名其妙。如有人问“小”字怎么写,我答道:竖钩、撇、点,对方说“错”,因为她孩子的老师说,第二笔不是“短撇”,而是“左点”。
还有台海两岸,用词习惯有所不同,也是个问题。比如台湾多用“卯劲”“卯足全力”,大陆多用“铆劲”“铆足全力”,两岸合编的《两岸常用词典》特别说明“铆劲”“铆足全力”的“铆”,在台湾也作“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台湾新闻是用“卯”还是“铆”呢?还有一个台湾常用的司法用语“三审定谳(yàn)”,新加坡的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常把“谳”误作“献”。
在日常工作中,时常碰到诸如此类的语用问题,身边没有一位“不会说话的老师”,就很难应付。
说起“不会说话的老师”,还真令人钦佩。他知识渊博,满腹经纶,却默不作声,有求必应,释疑解难,永不言倦。说句老实话,要是没有这位老师在身边“罩着我”,我想,是很难做好自己的工作的。
如今,我退休多年,赋闲在家,阅读写作,打发时间,在读写中难免会碰到这样那样的语文问题,因此案头依旧放着常用的字典和词典,并且老是要查检。
说到“老是查字典”,就想起一个故事。
话说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夕,三位语文专家专诚拜访了著名的语言学家、作家、文学翻译家季羡林教授。这一年,季老已经87岁了。在交谈中,精神矍烁的季羡林教授围绕学习中文和外文的问题谈了很多十分深刻的体会和意见。后来,季教授应访问者之请,把他的谈话写成文章——《关于学好中文和外文》,发表在当年的《语文建设》第7期上。

《语文建设》第7期(1998年)
季羡林教授在文章的结尾写道:“朱光潜先生是大学者,是我的老师。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对我讲,我现在老是查字典,我听了很吃惊。现在我也常查字典。不论是搞中文的,还是搞外文的,都应学到老。”
啊!大学者如朱光潜、季羡林教授还“老是查字典”或“常查字典”,在下不才,忝为语文工作者,岂能不把字典词典放在案头,随时查检?“老是查字典”不是一件难以启齿不光彩的事儿,我们应当养成勤查字典的良好习惯,像季羡林教授说的,活到老,学到老。
我在新加坡工作期间,编辑部的同事,无论记者、编辑或翻译,谁的办公桌上不放着几部厚厚的中文、英文或英华双语词典呢?这可不是摆设,装门面,而是随时要用的。有的词典书口已经乌漆墨黑的了,有的连封面都快掉下来了,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事有凑巧,日前收到老朋友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余惠邦先生发来的微信,余先生告诉我,在国庆60周年那天,他给正上中学的孙女和外孙各送了一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并在扉页写道:“这是每一个学习汉语的人必备的辞书。”于是这部词典成为两个孩子翻得最多的书,书脊都破了,用透明胶纸糊着。后来他们都考上了双一流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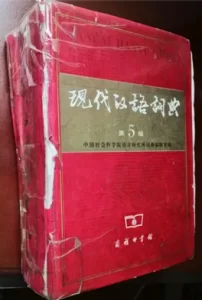

余惠邦教授送给外孙的《现代汉语词典》
养成查字典的习惯,日积月累,如果有人问起同样的问题,就胸有成竹,立马可以回答了,于是有的人被喻为“活字典”。其实,所谓“活字典”,是人家长年“厚积”的结果。
出了校门,老师就不在身边了。一典傍身,老师就在你左右了,而且寸步不离,使你受益无穷。
最近笔者在自媒体上看到有人撰文,指这个词用错了,那个语用错了,其中举“负增长”为例,说“增长”怎么能“负”呢?事实是它“负”了,你又怎么着呢?“负增长”早为《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2005年6月)所收录了。
更有甚者,本月初自媒体上盛传着一篇批评中央文件“错词白字连篇”的文章。我查阅7月18日新华社所发的通稿,文件并无文字错误。“错词白字连篇”从何说起?作者在文末还奉劝“秀才们要好好读书”。为蹭流量,这种下三烂的事也做得出。这位“秀才”还真的必须“好好读书”,在未学会做人之前,还是免开尊口的好。
不爱查字典,或懒得查字典,却好为人师,喜欢批评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并且十分高调,十分自信。到头来,被批评者搬出辞书,放到他们面前,才使他们哑口无言,尴尬万分。原来,错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这样的事,我在新加坡工作时也曾遇到过几次,而且批评新加坡人者都是我的同胞,他们从汉字汉语的故乡来到异国他乡,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地大发议论,夫复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