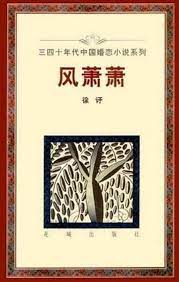四四
但阿美送咖啡进来,我就立刻惊醒了,我以为是白苹回来,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理使我心狂跳。
“惊醒你了?”阿美说。
“怎么我就睡着了?”我说:“白苹还没有回来?”
“我想就会回来的。”阿美说着出去,剩我一个人在房里,我喝了咖啡,吃了土司,又吸支香烟。最后,我倒在沙发上真的入睡了。
没有风雨,没有太阳,似乎是黄昏,我踏着白雪上山。没有飞禽,也没有走兽,雪上没有一个脚印,我看着我的脚从雪里埋下去,浮起来,一步一个印的走上去,回头看看整个的山上只有我的脚印。我非常得意的继续往前走,往前走,但不知怎么,好像踏到一个陷阱一样,我突然堕入深坑,似乎所有的雪都化作了水,从我的头上倒下来,我倒在坑底,让所有的水倾在我身上。我想山上所有我留着的脚印都该消灭了吧,但是水不断的下来,我感到冷。于是我感到有人把毯子盖在我的身上,是白的,白得同雪一样,是用雪编成的毯子么?我心里想,我用眼睛细辨,我清醒过来。
是白苹,她正用纯白的羊毛毯子盖在我身上,我发现我枕在沙发边上的头已经滑下,我像蜗牛般的在沙发上面蜷缩。
“白苹!”我把头移上沙发边上。
“是的。”一个百合初放的笑容:“昨夜我伤你心了,是么?”
“不。”我说:“是我伤你心了。”
白苹坐在我的身边,从她的面容表情,我断定她并未发现文件的失踪,但是我有良心在那里跳跃,一种惭愧感激与凄凉的情绪,使我的眼泪从心头涌到眼眶。我说:“原谅我这次。如果有什么危险的话,请随时告诉我,我愿意为你去死的。”
“……”她低下头,用洁白的手绢揩她晶莹的泪珠。
“白苹,不要留恋上海了。”我握她的手,抚握她手背与手心,我说:“伴我到后方去,让我们在民族怀抱里发挥我们的热情。”
“……”她点点头。
“真的,白苹。”我兴奋了。
“自然。”她冷静地说。
“那么什么时候去呢?”
“我想,我想……唉,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她沉着而冷静。
“为什么?”
“不要问我。”她说:“但是或者你先进去,我以后也许会进来。”
“不。”我说:“要去就一同去。”
“那么你等我就是。”她说:“但这是渺茫的。”
“那么,在我还留上海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们常相会相谈呢?”我说。
“自然可以。”她就站起:“现在,你再睡一会吧。”
“不。你也应当去休息了。”我跳下沙发,我说:“让我回家去睡,明天我再来看你。”
【二十五】
我想不说穿一个人过错,是容易使人改过的。那么白苹的态度该是觉悟了?
但是并不,从第二天起她再不提起这事情,而她的生活依旧,交际依旧。所不同的,是我参加了交际的活动,在许多场合之中,我变成了她的保护人,在许多场合之中,我又变成了她的秘书,在另外许多场合中,我又成了她的舞客。
起初还有我私人的意思,是想阻止她不再堕落,鼓励同我内行。如今则只有梅瀛子所吩咐的职务了。
梅瀛子在巧妙的场合中,让我认识了一个日本的巨商本佐次郎,叫我假装着与他们合股营商,又叫我与这两个巨商一同为白苹捧场。后来,为商务上便利的名义,由这两巨商宴请了许多日本军官,应酬往还,几次以后,我的世界已经与白苹打在一片。但是梅瀛子则永远躲在幕后,她认为我的交际与活动非常成功,可是并没有指派我什么特殊的工作。
在社会上,我已经以一个发了点财的商人姿态出现,似乎我也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奸商,不但日本人对我没有怀疑,就是我自己也时常怀疑到底我的生活是否是一种工作。
在这种生活开始的当儿,白苹有时候常常提醒我:“怎么?你完全变了!”
“为什么你可以跨进的社会而不许我跨进呢?”我总这样说。
“你同我比。”她冷笑地生气了。
“等你放弃你这个生活时,我也放弃。”
“好的,你等着吧。”
这样的对白以后,我们总是不谈下去,也许会怕对方伤心,也许会怕对方怀疑。我们继续过我们的生活。
但是如今,我与白苹已经不谈这些。在许多地方,我暗暗地保护她,在许多地方,她也暗暗卫护我,但整个的心灵则越来越远,虽然生活常常哄在一起。
不错,生活上常常哄在一起,但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则越来越少,也许机会并不少,而是我们没有单独在一起的需要,遇到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过去互相关切与期望的心理了。
日子这样的过去,在交友中,我在白苹身边的地位,已经是到了无人妒忌的境界。这完全是白苹在交际上的优势,在许多日本军人中间,她总是抢到主动地位的。从情形上看,起初也许有人对她怀有特殊的企图,但现在她只成了他们交际的偶像,我自然也不过是她群众之一,假使悄悄地比别人接近的话,完全为我认得她日子较久,在她的旁边,有一半侍从的性质,譬如在许多人的集会中,白苹常常指挥我做零碎的事情。所以很自然的当夜阑人散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日本军官要陪她回家的话,据说在过去她总是拒绝的,而现在她则常常接受,同时一定用命令口气对我说:“一同去。”
“我不去了。”我故意说。
“去,”她说:“明天我要请客,我要你为我设计。”于是我就服从着跟去,而几次以后,送她回家则成了我固定的差使。
这样的差使已经是没有人妒忌与羡慕,在我也不以为光荣,常常在汽车里一句话都没有,送到以后,说一声“再会”就听她下车,很少再上去在她的家里静谈的。
有一天,是一个日本军官请我们在霞飞路上吃日本火锅。大家吃了点酒,席终时,许多人都主张去跳舞,但是白苹一定要去赌场,而赌场是日本军人绝对禁止去的地方,于是有一个军官叫做有田大佐的提议到他家里去赌,这是过去所没有过的事情,可是白苹接受了。我在与白苹关系上需要同去,在我暗中的职责上也要跟去。座中有田大佐与武岛少将是有汽车的,于是我们就分坐着这两辆汽车。我根本不知道有田大佐住在什么地方,后来我知道白苹也似乎并不知道,车子一直驶到虹口,从北四川路弯到施高塔路去。
在一个很大的巷堂前开进去,有田大佐用低级的上海话对我们向导,告诉我们前面住的都是小军官,每人占一层两间,后面高级军官则是每人一幢的,于是就在里面一幢房子前面停下来。有田大佐得意地带我们进去,会客室居然挂着中国画,家具都是西式的,地毡则是旧的,这无疑都是掳掠来的东西。有田大佐很有礼貌招待我们,并且指挥佣人在楼上预备赌具。接着我们就跑到楼上去,在分配座位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在窗前立了一会,这窗户正对着前面房子的后窗,那窗子有白纱的窗帘掩在那面,但灯光把两个人影投在窗上,我自然注意了一下;似乎是一个男子在追迫女子,女子害怕地在退让,又似乎男的是一个日本军人,女的是一个西洋人,又似乎……我大吃一惊。
“看什么?”白苹走过来说。
我按捺一切的惊慌,不响,在白苹走到我身边时,我深沉而确切的说。
“看。”
白苹楞了。
“认识吗?”
白苹几乎快失声了。我冷静地提醒她:“镇静!”
但是前面的影子已使我无法镇静,因为女的已经快在男的掌握中了。我正想提醒白苹赶快救她的时候,白苹已经嚷出来:“海伦!”这声音很急很响。我吃了一惊。
“白苹。”海伦厉急的答应,渗杂着恐怖的声调。
我看见一只粗野的手按她的嘴。我的心直跳,但极力抑制着,想用冷静的理智求一个妥善的方法,可是白苹竟改用活泼高兴的语调说:“巧极了,海伦!”她说:“白苹在有田大佐家里呢!”
有田大佐以为是谁,他也走到窗口来,但是白苹反身迎住了他,她说:“是我的朋友,巧极了,去叫她一同来玩。”她说着就拉着有田大佐往楼下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