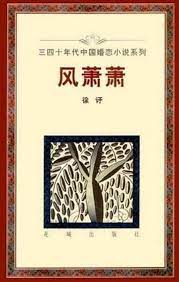四一
“我想你一定太忙了。”我说着来回的踱步,四周看看,我说:“这房间经这样一布置,似乎更加庄严了。”我好像不经意的走向套间去,我又好像不经意的打开门,我一面走了进去,一面说:“这里还是箱子间?”
“都是别人寄存的。”白苹说着走过来。我故意推动着报纸,我说:“你还保存报纸?”
“唔……”她在我身后回答我,我回过头去,看见她百合初放的浅笑。
这笑容使我想到我们过去的感情与距离,我顿悟到今天的谈话显得我们过分的距离了?抑或是我今天的行动使我自己失了常态?还是她对我的态度本质上有什么变化?
在我,站在正义的立场,我自信我的行动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过去完全信任我对我有无限友情的人面前,我深深地对我行动有点惭愧,照我平常的态度与气质,我一定用最真的情感来对她诉说,最正直的理论来使她折服,我要叫她自动的把那文件交给我,让我带给梅瀛子,但是这是梅瀛子再三叮咛过我,而我应遵守的禁条,同时,我已经偷获了文件,已失去了我可以忠于朋友的资格。就在她一笑的瞬间,似乎有一种灵感袭来,我用非常真诚的眼光,从她的嘴角望到她星光般天真的眼睛,我一手挽住了她的手臂,伴她走出套间,我用喉底的语气说:“还当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自然。”她笑了。
“但是我现在想离开上海了。”
“后方去么?”
“是的。”
“我早就这样劝你了。”
“我希望你同我一同去。”
“原来你不去是为我了。”她撒开我的手,嘹亮地笑着,倒在沙发上。
“事实上我不放心你。”我庄严地坐在她前面的脚凳上,冷静的说。
“你在这里,倒使我很不放心。”她突然严肃起来。
“但是你一直没有打电话叫我来看你。”
“因为我忙。”
“忙,”我说:“这就是我不放心的地方。”
“为什么要对我不放心呢?”她说:“我是一个舞女,忙就是我的收入。你应当放心才对。”
“你讲收入?”
“自然,我告诉你,你到后方去可以做应当做的事,我去不过是消耗。”她说:“我希望你不要为我想什么,你自己好好的走吧,需要钱,我这里来拿。”
“你以为我是来问你借钱的么?”我站起来。
“怎样,”她说:“问我来借钱是耻辱么?”
“不是这样讲。”我说:“我要问你借钱我就干脆的借,何必同你说这许多别的。”
“那么你来劝我同你走了。”
“是的。”我说:“我想知道你的意思,因为我已经料理好我的一切,如果你不走的话,我也决定不走,那么以后我要常常见你。我们似乎不应当这样难碰到。”
“那就随便你了。”她说着就站起来走出去。
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心中有许多紊乱不安的情绪;白苹的态度似乎是自暴自弃的堕落,但是对我殷殷期望,始终是我所应当感激的,站在最高的友谊立场上,我必须对她坦白地作最诚恳的劝告,但这正是我职责上所不允许的。我猜想她是十二点回来的,阿美应当还未就寝。她进来脱去大衣,也许会见过阿美,也许在衣架上看到我的衣帽,所以能够从容地开门进来,从她的表情上看,似也并没有对我的使命有什么怀疑,我很希望我可以马上离开这里,到梅瀛子地方去,早点可以把原件拿回来放在原处,但是一时似乎没有脱身的办法。
我现在思索我是否遗留了什么可疑的痕迹,我已经在她面前到箱子间去过,那么假如里面灰层上有我痕迹,一定再不会怀疑在她来了以前我有什么探索了,其他呢?抽屉里似乎不会有什么,假使有浮面的移动,也只是我一个人在期待中偶然的动作。于是我想到书架,我视线立刻注意到Faust上面,我忘了我取文件以前的样子,我竭力追想当时的样子与现在比较,似乎觉得那书的两面松了一点,但是我立刻意识到这也许是神经过敏的幻觉。
“徐,到这边来坐吧。”这句话提醒了我白苹刚才出去的意识,我站起来开门出去。
白苹已换了灰布的旗袍,手里捧着刚才阿美预备好的食物,走向她自己的寝室,我跟着她进去。
白苹在圆桌上铺好台布,我帮助着放好夜点。她又拿灯桌上刚才阿美放好的白花瓶,放在圆桌上面,灯光下这花有特别的风姿。白苹坐下,万种安详的表情聚在眼梢,眉心中放露几分疲倦,她微喟一声,喝一口茶说:“谢谢你还关注我。”
“你已经忘了我。”
“我忙得把什么都忘了!”她说着头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这印象使我想起了我同她从杭州回来火车上的轻睡姿态,我忆起那天我为她画的像,这几张像在我记事簿里,我一直把它忘去,后来这本记事簿抛在抽屉中,记得搬在白苹地方时,就已经没有见到过,现在更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了。这记忆实在有点奇怪,因为它一方面使我对白苹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我感到白苹对我始终没有带一点不好,而我今天,就利用她对我历来的感情,来偷她的文件,有一种惭愧从我心头浮起,我觉得我有坦白地同她说明的必要,但是另一方面似乎有一种力量牵制着我,我望着白苹倦怠的姿态,听凭两种不同的力量在心头激冲,最后我终于开口了,我说:“白苹!”
这突兀而苦涩的声调使白苹张开眼睛,振作了一下,我说:“假使你在上海这样下去,你一定会被人利用,说不定最好的朋友就成了敌人。”我语气太生硬,声调太苦涩,在说出以后我才感觉到。
“你是说你同我吗?”白苹振作了一下,坐直身体,微微露出笑容。
“我想假使我进了内地以后,你一直在这里……”
“我倒很喜欢我的敌人里有一个是我的朋友。”她说:“并且也很想我的敌人有一天又做了我的朋友。”
“我虽然喜欢敌人做我的朋友,但不喜欢朋友做我的敌人。”
白苹低头沉默许久,忽然站起来,她踱出了座位,话不对题的说:“这些话我们以后不要再谈,人与人中间也许有爱,但人与人中间不能有了解。”
“你以为我不了解你么?”
“我自己也不了解自己。”她走回来说。
突然,她坐在另外一个沙发上,面部带着痛苦的表情,头靠在沙发背上,两手蒙上了脸,半晌不动。
这表情使我觉得是一种良心的发现,这时候,似乎是最好进劝告的机会,我决心违背梅瀛子的叮咛,准备用最诚恳的态度,叫她告诉我她错误的行为;用最坦白的心,对她供认我今夜的使命。我悄悄的过去,俯身下去,在她的耳跟说:“白苹,你悲哀了?”
她不响,不动,我胸前所藏的文件使我姿势非常不造,我激荡一种奇怪的情感,跪在她的座前。
“白苹,告诉我,为什么忽然这样呢?”
她啜泣起来。
“白苹,当我是你的朋友,把你的心告诉我。”
她似乎用整个的意志在克服她的情感,她隐泣着。
“白苹,让我们彼此坦白,”我说:“让我们一同到后方,到山乡去做教育工作去。”
她似乎已将感情克服,恢复了不响动的凝结。
“白苹,假如你一定对政治工作有兴趣……”
“废话!”她叫出来,马上站起,推开了我,冷静地说:“你回去吧。”
“白苹……”
“让我一个人。”
“白苹,难道……”
“我需要孤独。”她冷静地坐在另一个座位:“你出去!”
“不能让我再说几句话么?” (待续)